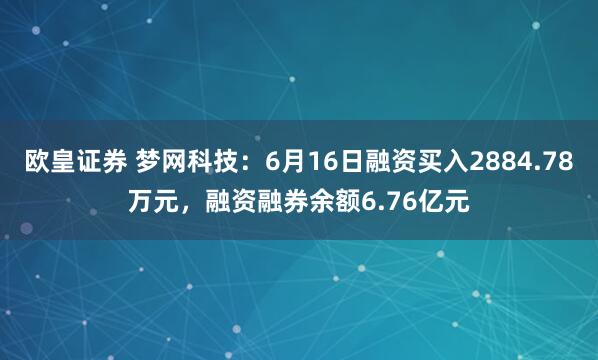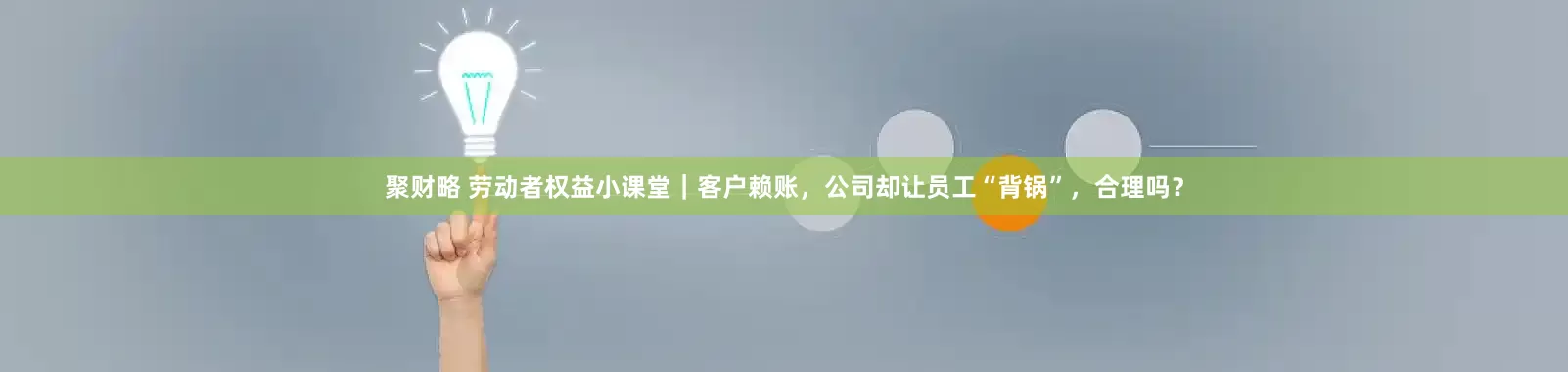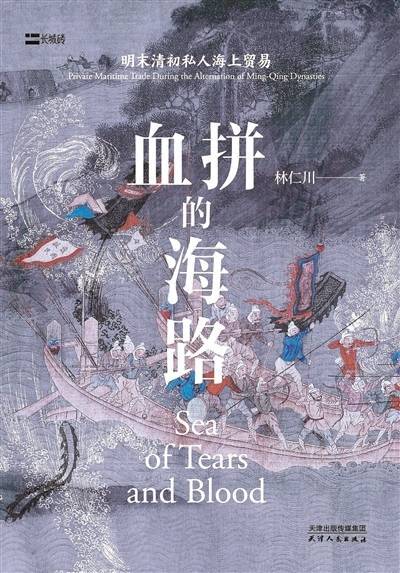
◎唐山牛盈服务中心
“以海为家之徒……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,视军门如世代仇雠。”嘉靖二十五年(1546),名将朱纨始提督军务,负责剿倭。让他震惊的是:当时倭寇以漳泉人为主,真倭“仅十之一二”,沿海民众、乡官多通倭,遂生此叹。
朱纨的剿倭战绩不俗,却引沿海势豪贵家大哗,他们嗾使御史陈九德弹劾,朱纨被罢官,自杀而亡。他说:“漳泉地方,本盗贼之渊薮,而乡官渡船,又为盗贼之羽翼。”
朱纨不服气,因他没意识到,自己撞上了人类史的“失控时刻”。
十四五世纪,因商品经济发展,全球多处出现“资本主义萌芽”,如欧洲的威尼斯、热那亚、比萨、佛罗伦萨和米兰,以及中国的江浙闽粤。1453年,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(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),东西方商路被切断,地中海诸国陷入停滞牛盈服务中心,大西洋沿线的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等开始探索新航路。与此同时,明朝海商也在突围,先后出现许氏兄弟集团、王直集团、徐海集团、萧显海集团、何亚八集团、许栋—许西池集团、洪迪珍—张维集团等,而郑氏(郑芝龙、郑成功)集团堪称巅峰,最多时“水陆官兵计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名,大小战舰约计五千余号”。
东西海商有共同点,即亦商亦盗,能抢则抢,抢不了才经商。不同的是,西方海商不全靠私人资本,国王也参股,并予政策扶持,故能公然“仗剑经商”。中国海商却套着“朝贡贸易”的紧箍咒。1511年,葡萄牙海商占领马六甲,堵住中国海商通往印度洋的通道;1603年、1639年,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商两次大屠杀;1652年,荷兰在台湾屠杀华人……华商几无还手之力,明政府亦无强力回应。
一个个海外市场丢失,明政府却在打压境内的自由商港。双屿港、舟山岑港、月港、晋江安平港等均未逃过“崛起又衰落”的命运,朱纨占领双屿港后,竟聚木石塞港,使“贼舟不得复入”。
这是因为,明初即厉行海禁,已成“祖宗之法”。海禁的主要目的是防倭患,却越防越严重,嘉靖年间达极致。正如书中钩沉,嘉靖时,日本“应仁之乱”已过七八十年,社会渐安定,且“倭寇”少骚扰较近的山东和辽东,反集中在较远的东南一带,可见真倭不是主流。
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后,社会两极分化加剧,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,投入海洋贸易,却不被王朝允许牛盈服务中心,只好与“倭寇”合作,进而假冒“倭寇”。
明朝统治者长期未意识到“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,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”(李贽语)之理,落入“强化秩序—遏制生产力—穷人增加,铤而走险—秩序受冲击”的怪圈中。
美国学者凯文·凯利在《失控》一书中提出惊人观点:进步始于“失控”,正是一次次“失控”和“控制”,构成历史的波浪式发展,关键在把握好临界状态。换言之,在“控制”中,应给“失控”留下空间。
朱纨之败,正在于他未把握住“失控时刻”赋予的机遇,反而站在生产力进步的对立面。
隆庆元年(1567),福建巡抚涂泽民“议开禁例”的上疏被采纳,明穆宗解除海禁,致“海禁开,倭寇止”,直到明亡,“倭寇”再未成患。
明末清初,中国对日本和南洋,每年进出口货物总量便达13.765万吨,贸易总额达1647万两白银,加速了向近代化转型的步伐:湖州“隆万以来,机杼之家相沿比业,巧变百出”;苏州城内“居民大半工技”;景德镇“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,每日不下数万人”……而美洲新植物如玉米、番薯、苦瓜、花生等“种先来外国,栽已遍中原”。
然而,从传统到近代,是人类史上一次惊人的跨越,仅靠“隆庆开关”远远不够。政策改变不等于深层变革,“隆庆开关”无法解决陋规重、海商受打压、定价机制扭曲、商业资本薄弱等问题,放开的海路仍是“血拼的海路”。强如郑氏集团,在清代“迁海令”打击下,也出现严重亏损,无法再与西方海商争夺市场主导权,随着对方掌控了航线、定价权、货源、市场份额等,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凋谢。
本书表明,中华文明从不缺乏海洋意识,但把“好的意识”转化为“对的结果”,还需思想方法、决策机制、管理手段、把握机会能力等的跃迁。
“海洋贸易史”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,《血拼的海路》(林仁川著牛盈服务中心,天津人民出版社,2024年5月)胜在资料详实、内容扎实,每一句都有来历,都让人读后放心,体现了老一代学者厚积薄发、平易近人的非凡功力。
天盛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